
沈善炯院士伏案工作 ■ 资料图
1、苦难读书日 心怀报国愿
“沈先生求学之际,正是家国动乱、社会动荡之时。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连连败退,多数学校、国民也不得不随之迁移,沈先生就是在各处转学、借读中求学。一路兜兜转转,他终于来到云南,通过了西南联大的转学考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熊卫民,因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与沈善炯结缘,曾为沈善炯整理口述史,并撰写了沈善炯的传记。
熊卫民介绍,在西南联大,沈善炯在教授张景钺和陈桢的引导下,对植物发育、世代交替、遗传学、苔藓繁殖等产生了极大兴趣。
1942年夏,沈善炯从西南联大毕业,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病理组,跟随戴芳澜教授开始了古瓶菌的形态与生活史研究,勘正了前人对古瓶菌描述的一些错误。他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于1944年4月发表在《美国植物学杂志》上,这是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
1947年,沈善炯前往分子遗传学的诞生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离开祖国前,沈善炯在西南联大的恩师张景钺嘱咐道:“我等待你,望你学成回来。”这句话如千钧之重,时常萦绕在沈善炯的耳边。
到美国后,沈善炯不敢懈怠,记住恩师的教诲,决心要早日学成报国。
1950年6月,沈善炯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之后,他本想继续进修,多学习些知识带回祖国。然而,很快有消息传来——美国政府取消了加州理工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禁止其离开美国。
沈善炯大感不妙,立马作出决定,拒绝国外导师的进修邀请,订下近期回国的船票。尽管如此,归国过程还是发生了意外。
在日本横滨、东京两地,沈善炯遭遇了美国陆军部的扣押。然而,他心中始终怀抱着早日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愿望,从未屈服。数月后,沈善炯才被释放回国。
2、打破技术封锁 攻克金霉素研制难关
“到80多岁时,我常常想,我这一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科学,一个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晚年时,忆及自己的人生,沈善炯如是说。纵观他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武器、飞机、石油等军事资源遭到封禁,同样在禁运名单的还有抗生素等医疗资源。中国必须迅速开展抗生素研究并实现产业化,以满足医疗、经济等各领域的迫切需求。
当时,金霉素的生产一直被美国垄断,其他各国建厂必须与美国工厂合股投资,全球只有美、英、意三国拥有金霉素生产药厂,我国的金霉素全部依赖进口。
沈善炯刚刚摆脱了美国的阻挠,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了祖国的需要,尽管对抗生素研究并无任何经验,沈善炯仍然担下重任。他觉得,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自己责无旁贷。
为此,沈善炯和团队成员来到我国第一家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沈善炯把工厂的工人当作学习和研究抗生素的启蒙老师,常到工厂请教有经验的技术员和工人,虚心向他们学习发酵、提取和鉴定等基本操作,结合国际上已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文献展开思考研究。
在研发过程中,沈善炯带领着学生和助理们反复地进行实验,并详细记录实验数据。但由于工作缺乏经验,在进行多次发酵试验后,都没有获得一个可以重复的可靠结果。
在一次抗生素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应当注意发酵条件的研究。沈善炯从中获得启发,决定转变工作方向,着手对抗生素发酵上一直被人忽视的接种条件,即接种培养基,接着展开研究。
经过沈善炯团队两年多的努力,我国的金霉素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1954年,由上海工业试验所、上海第三制药厂承担的金霉素扩大生产试验工作启动。临床试验发现,国产金霉素副反应很小,成功达到了临床使用的要求。
1957年,金霉素在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我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能够生产金霉素的国家,金霉素的发酵单位、产品质量等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3、老骥伏枥 开辟生物固氮新领域
早年为了国家,放弃遗传学方向的研究,转而攻坚国家急需的金霉素研究,年近六旬时,也是为了国家科研发展的新需求,沈善炯在1973年又受命组建新的研究组,开辟新的方向,从事生物固氮研究。
自博士毕业回国以后,沈善炯一直脱离遗传学的主流研究。为了尽快赶上世界研究进展,沈善炯便成天泡在图书馆里,找寻、阅读和抄录遗传学文献。实验室设备落后,条件有限,沈善炯就用一个冰箱、几套培养皿和一些吸管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实验,向年轻组员演示教学。
短短三年内,沈善炯等人就发现了新的固氮基因,证明了固氮基因在克氏肺炎杆菌染色体上呈一簇排列,否定了国外科学家认为基因间存在“静止区”的观点。这一研究成果很快得到发表,并在国际上被大量引用。
沈善炯在国内开辟了分子遗传学和生物固氮领域,固氮基因表达与遗传操控方面的研究赶上国际前沿水平,对nif基因的启动子的结构和调节的研究也获得了高度评价。经过三四年的奋起直追,分子遗传研究室成为国际上以研究生物固氮而知名的实验室。
1980年,沈善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
沈善炯在美国上学时的老师和同学都有获得诺贝尔奖,而学业优秀的他却选择回国。
也曾有人问他此生是否有遗憾,沈善炯说:“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有得诺贝尔奖的,我向来好强,在那念书时可并不比其他同学逊色。”然而他接下来的话却更震撼人心:“但是,论起对中国的贡献,这些跟回到自己的国土去建立实验室、培养学生,使科学在自己的国土开花、结果,还是不能相比的。”
治学名言
沈善炯心语
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西南联合大学。它是“民主堡垒”,风气非常好,既严肃又自由,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老师和老师之间,关系非常融洽。大家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觉得自己肩负抗战胜利后重新建设中国的使命。虽然条件简陋,但同学们学习非常刻苦。我的挚友申泮文常说,爱国主义出英才,我很赞同。
如果说西南联大教我怎么做人,那么加州理工则教我怎么做科学。在那儿,竞争和合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家都在为真理而奋斗。
不能排斥自由研究,不能动不动就去批判别人,中断他们选择的研究。科学上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精神建立不起来,这是致命的。
在留学异国的年代,我的老师哈洛威常常提醒我:“沈,中国需要你!”我感谢他把对我的希望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童年时的梦,老师的教诲,使我明白一句名言——“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其祖国”的真谛。这是我努力求知,希望能报效国家的志向的源泉,也是我突破万难,回到祖国的动力。
我有道德学问高尚的恩师,他培养我入科学之门;我有愿意献身科学、报效国家的学生,他们鼓励我对科学执著追索,做个有用之人。夜来扪心自问,我真不愧此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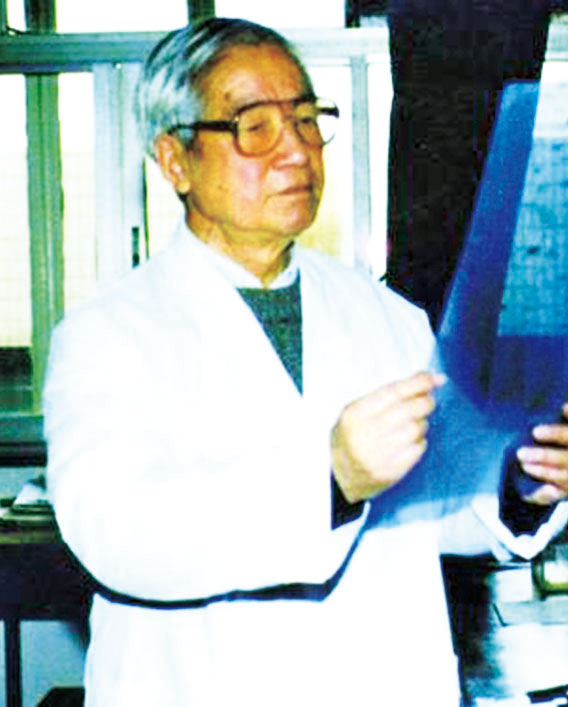
沈善炯院士在实验室检查实验结果■ 资料图

沈善炯(1917年4月13日~2021年3月26日),我国著名遗传学家、微生物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细菌固氮基因的结构和调节及根瘤菌和宿主植物间相互作用的遗传学关系研究,在抗生素、细菌的糖代谢、细菌的氮代谢、固氮基因的结构和调节、根瘤菌共生固氮等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
延伸阅读
“我的科学生涯”
沈善炯在回顾自己从事科研工作几十年所走过的路时,认为自己这辈子在学术上谈不上有什么成就和贡献,只做了三件事:
一是和中国科学家一起参与新中国的抗生素研究;
二是为中国传统的偏重于医药和工业发酵方面的微生物研究引进了现代微生物学方面的内容;
三是在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工作也开展得较早并帮助筹建了上海交大生物系。
1997年,80高龄的沈善炯,精力已大不如前,但他想发挥余热,便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把他的经验和教训留下来。2001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的科学生涯》。
沈善炯一生痴迷科学,耄耋之年仍坚持带学生。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王彦章说:“直到90多岁,先生还坚持一周去三次实验室。我们为课题进展不顺而情绪低落或烦躁时,他的话经常能让我们感到峰回路转。”
宏图初展
1951年春,经谈家桢和丁振麟介绍,沈善炯去杭州,到浙江大学医学院从事生物化学的教学工作。后来国家进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被肢解。1952年2月,应殷宏章之邀,沈善炯改到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1953年独立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下称植生所)工作,任微生物生理研究组主任。
当时,中国的抗生素生产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并遭到一些发达国家禁运。为解决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沈善炯无条件服从国家需要,带领几位研究技术人员从零开始,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他们主要承担金霉素和链霉素的生物合成任务,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即做出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既有学术价值又能指导生产实践的重大成果。
1958~1959年,应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秘书长之邀,沈善炯访问苏联医学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一年。回国之后,他即在植生所微生物室的基础上着手组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1962年又并回植生所),并以副所长的身份主持该所的工作。
当时上海微生物研究所成立了五个研究组,分别研究微生物的生长、代谢和遗传,以及自养菌和噬菌体。除主持全所工作之外,沈善炯还具体负责代谢和遗传这两个组。沈善炯对工作极为投入,由于过于劳累和缺乏营养,他一度患了严重的肝炎,不得不经常住进医院。
在这一时期,沈善炯培养出了以王孙仑、洪孟民为代表的一批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并带领他们取得了一批得到国际承认的重要成果。譬如,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中间代谢产物甲基1,2-醛,证明己糖分解可以循甲基1,2-醛-乳酸的支路代谢进行;在研究链霉菌时,他们发现了作用于烟酰胺辅酶的烟酰胺核酸酶和能使木糖转变为木酮糖的D-木糖异构酶。



